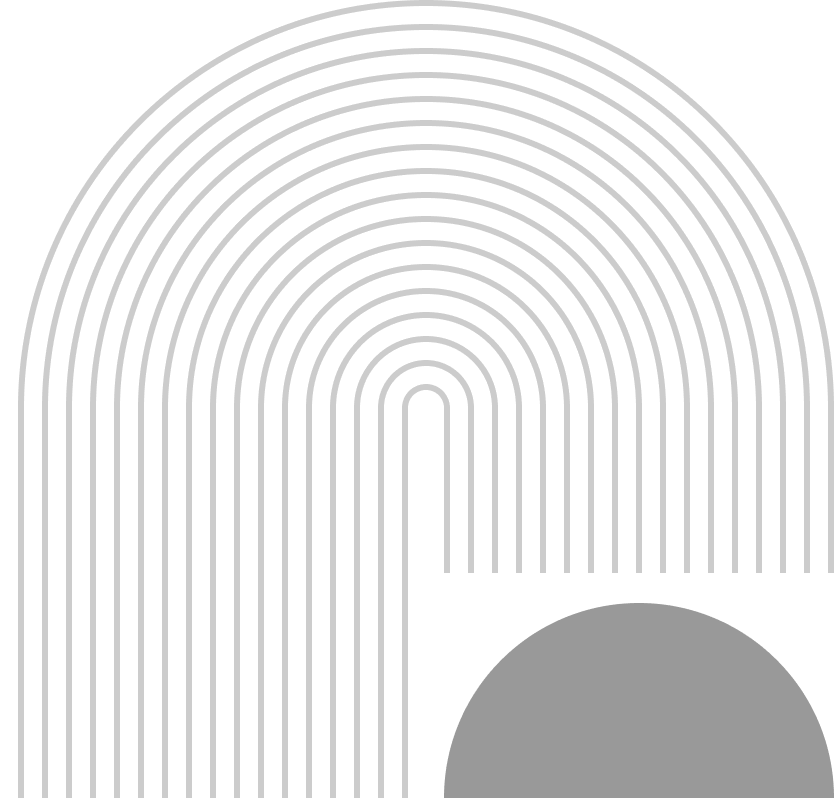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之不利形势,宣布将政府迁往其甫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盟军自日本占领领土台湾的首府台北市。进入1950年代后战事渐歇,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的格局型成。政府迁台后实施长年戒严令的时空背景下,仍有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公开主张做为国家元首的中华民国总统应由居住于政府实际统治领土的人民直选产生。
1964年9月,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和魏廷朝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主张“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三人随即遭逮捕、以“叛乱罪嫌”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因为戒严限制,《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在党外并未流传。1971年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1972年1月雷震所提出的《救亡图存献议》中亦有“总统由海内外人民直接选举,或由监察院立法院合组联席会议选举”之主张。1975年参加第二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的知名党外运动人士郭雨新也曾提出“总统及台北市市长直接民选”之政见。
进入1980年代,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自由派学者,为了对抗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威权总统,诉求“回归宪法”,换句话说就是回归《中华民国宪法》内偏向内阁制之政体。直到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建党之前较少有总统直选主张。1986年党外运动人士洪奇昌、翁金珠、黄昭辉组织连线参选第三次增额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由林浊水建议,诉求“亲手选出我们自己的总统”,十分轰动,三人顺利当选。1989年姚嘉文领导“新国家连线”参选第六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继续诉求总统直选,并由林浊水任总干事,连线公布总统直选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草案采取奥地利与爱尔兰等的倾向内阁制的双首长制。直选目的在于透过直选创造台湾主权独立象征,而不在建立总统制之政体。1990年,民主进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总统直选主张,并先后起草了《民主大宪章》和《台湾国宪法草案》。此后民主进步党发动一连串总统直选街头运动。
1991年4月李登辉总统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第一次增修)确定国会在台湾全面改选并于1991年12月举行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92年3月,新当选的民主进步党及无党籍国民大会代表合组“总统直选联盟”,向政府高喊“总统直选”。4月,第二届国民大会在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中山楼集会,民主进步党代表于会议进行中拉布条要求总统直选。4月19日,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与林义雄等人率领数万群众游行与静坐要求总统直选,历经三天两夜在台北车站等地前的街头抗争,施因“四一九游行”被以违反“集会游行法”判拘役50日。5月10日成立“新台湾重建委员会”,推动新宪法、新国家和总统直选。[4]
在各界讨论修宪时,包括李焕、郝柏村、邱创焕、马英九、关中在内的中国国民党保守派人士坚决反对总统公民直选,主张仍由国民大会选出。因改革遭遇党内阻力,1992年5月27日第二届国民大会临时会通过之宪法增修条文(宪法第二次增修)仅载明“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之,自中华民国八十五年第九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实施”,而对选举之形式仍未有定论。之后中国国民党保守派人士其后于民意压力下,再主张改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之“委任选举”,但最终不敌支持公民直选的呼声。[2][5][6][7][8][9][10][11][12][13]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迁台后,政府实际管辖领土范围与台湾省高度重叠。虽然后来成立台北市与高雄市两直辖市但是台湾省仍管辖高达98%以上的面积与80%以上人口。1992年5月宪法第二次增修后,将原本由中央政府指派的台湾省省长、台北市市长与高雄市市长改为公民直选,并预计于1994年12月举行首次省长与直辖市长选举。随后之修宪讨论中亦注意到民选后台湾省省长之权力基础已有与非直选的总统或行政院院长相抗衡之势。该情形类似1991年苏联政治中,由间接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戈巴契夫无法驾驭由直接选举产生有民意基础的俄罗斯总统叶尔辛,而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又称“叶尔辛效应”。几经折冲后,中国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达成总统直接民选的共识。
1994年7月28日,第二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临时会中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增修条文(宪法第三次增修)明定“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之”,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尘埃落定。1996年3月23日举行了首次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直接选举,这也是台湾人民第一次有机会以直接投票的方式来选出自己的国家元首。[11]